不知不觉,张朝阳的物理课已经开了一年多了。6月还出版发行了《张朝阳的物理课2》,大有一直坚持下去的势头。
高人气自然是让张朝阳持之以恒的动力之一,毕竟在搜狐新一季财报公布后,张也表示下一步的重点将是“用户获取”,而物理课背后对应的恰恰是搜狐的知识直播矩阵。
但抛开其上市公司董事的身份,仅从“人”的角度出发,我们能隐约从这位“不务正业”的知识博主身上感受到一种历经大风大浪之后的旷达。
历经多年起伏,这位学霸出生的大佬似乎终于回到了让自己最舒适的领域。但忠于个人志趣不代表不争,相反,短暂的停驻,是为了更好地出发。
2013年5月的最后一天,张朝阳带着一身疲惫和汗水从酒吧走出来。回想起那天董事会上他的失语和与会人员眼神中的不满,他又一次失眠了。这一年是张朝阳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年。事业陷入低迷,自己也患上了抑郁症。因为严重的失眠,他常常吞下3倍剂量的安眠药,但依然难以安眠。那年中秋节后,张朝阳“消失”了。这是自2008年之后,张朝阳的第二次闭关。在雨雾绵绵的蒙顶山上,他承包了一百多亩茶园,当起了地地道道的茶农。张朝阳换上粗布衣服和草帽的形象,想来多少有些违和感。要知道在十多二十年前,张朝阳还是一个地道的时尚主义者,围绕在他身边的也大多是“叛逆青年”、“花花公子”这类带着都市雅痞的形容词。曾经的张朝阳是放荡不羁的,这也正好接驳了他的少年得志。作为中国互联网的第一批弄潮儿,张朝阳创造了许多“第一”:拿到过中国互联网史上第一笔风投,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中文门户网站,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互联网创业者,张朝阳也被称为“中国互联网第一人”。再往前,便是在意气风发的学生时代。在清华读本科时,张朝阳已经是前1%头部学霸。考取李政道奖学金时,全国各专业加起来都不到100人,张朝阳是其中一个。回国创业后,张朝阳和丁磊、王志东并称为“网络三剑客”,风靡一时,而他是其中最张扬的一位。在公众视野中,他在天安门拍轮滑照片,为杂志拍半裸照,登顶珠穆朗玛峰;在私人聚会上,他自创“查尔斯狐步舞”,不遗余力地将聚光灯吸引到自己身上。豪宅、游艇、私人飞机……在那个刚刚脱离计划经济不久,世贸国门初次洞开的年代,张朝阳不断刷新着中国人对财智阶层的想象,甚至有媒体称他为中国版的“盖茨比”。这大概对应了那句,年少时行走江湖,书箱与剑、酒马相伴,不会寂寞。但真正的人生,说到底并不是那些清清楚楚的白纸黑字可以完全概括。雄心和现实交织、恣意和颓废混杂,这种复杂的况味不仅体现在盖茨比这个虚构人物身上,体现于背后作家菲茨杰拉德的真实人生,也贯穿了张朝阳的前半生。在世纪之初那个群雄四起的年代,张朝阳是互联网教父级别的存在,仅搜狐系就培养出300多位创始人,他为门户网站打开了一扇窗又一扇窗。在那些看得见的草长莺飞杨柳依依之外,被外界忽略的却是张朝阳呕心沥血、如饥似渴的工作状态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他每天只睡4小时,却可以工作十几个小时,工作内容涵盖无数通电话,还要应付各种各样的专访,30%的精力用于应付董事会,40%的精力用在产品上。在早年的诸多采访中,张朝阳丝毫不扭捏地表达了自己对财富与功名的向往,他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迎接名利的到来,但他还没有学会如何面对辉煌的渐行渐远。直到去了蒙顶山上,在那个盛产蒙山黄芽的小村庄里,他背朝黄土面朝天,和年近古稀的茶农坐在一起,把他所有的抑郁、痛苦与不安和盘托出,握着茶农的手泣不成声。在这片与世外“隔绝”的天地里,再没有无休止的市值竞逐,没完没了的升学考试。觥筹交错,人情冷暖,仿佛都成了上辈子的事。莫怕问了“佛法”,就会逃禅,这是世人很长一段时间对张朝阳的误解。面对搜狐的掉队,他在公众场合开始乐于承认自己的“错失”。他投资《煎饼侠》,自己也跑去客串了一把。去参加互联网大会时,他甚至可以公然打起瞌睡。他开始“严肃认真地跑步”,自称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就跑了900公里。2016年还在清华大学领跑了一场3000余人的马拉松。虽然依然讲述着“再造门户”的壮志,但务实的成分更多了,他认为“活下来”是复兴搜狐的第一步。他还给自己写了一段墓志铭:早期把互联网带向中国的几个人之一;创办了一个不错的公司;对物理的大众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;热爱运动和生活。有些时候不得不承认,所见所知越多,并不轻松,也不全是好事,因为容易认命,而这种认命并非全是坏事。张朝阳如今的确变了很多。如果是二十年前,张扬的查尔斯首先一定会把第二条的“不错”定为“一流”。但如今张朝阳不再执着于开疆拓土。他把物理课看作人生的第二曲线,同时也为搜狐另辟了一条蹊径——直播。不过不同于目前主流的娱乐化直播,因为有了张朝阳的物理课这张硬核名片,搜狐能在如今王牌四起的知识直播赛道树立起差异化,进而力求覆盖各个学科领域。而满足差异化需求的“价值直播”,也恰是搜狐一直在做的尝试。张朝阳没有耽溺于带搜狐重回第一梯队,这对搜狐而言并非坏事,君不见多少企业陷入市值困境后,激流勇进,勉强用一些自圆其说的故事来说服投资者。张朝阳由始至终都是清醒的,无论是对搜狐的处境,还是对昔日错失的风口。在很早之前他就对中国互联网的内容消费做出过这样判断:一是基于板块导航的消费,有频道有编辑,满足顶部需求;二是基于个性化订阅和推荐的消费,基于大数据,自媒体这类“连接”技术满足长尾需求,也就是“今日头条”模式;第三种是基于 SNS 的信息消费,也就是现在的腾讯新闻与新浪新闻,通过社交网站为新闻导流。新闻阅读需要一味的个性化吗?张朝阳并不认可。他认为一味的个性化,将导致推送内容的僵硬,因为很多时候人们对信息的索取是随机的。根据用户的点击行为推送信息,会让“新闻客户端会越走越窄”。客观来说,张朝阳的判断是正确的。算法推荐创造了巨大的成功,但它并不能代替人类思考,反而算法困境成为当代最大的信息接收威胁。近期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的一项调查中,就有62.2%的受访者直言,自己陷入了“信息茧房”。看见趋势是一回事,如何抉择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搜狐仅仅只是慢了半步,就被移动互联网狠狠地“被扇了两耳光”,这是时代的残酷,张朝阳愿赌服输。在2019年搜狐21周年庆祝活动上,他表示:“如果把一个公司的成长历程比作一场马拉松的话,半马刚好是21公里,我们刚刚过了半程。中国互联网的竞争已经完成了上半场,下半场也才刚刚开始。”张朝阳已经决定要将搜狐放置于更长线的竞争序列中,尽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,搜狐可能再难回到聚光灯下。但是怕什么,就像他对俞敏洪说的,“我们一起做百年老店。我们是长跑的,人活着就得搞事情。”张朝阳是酷爱长跑的,而无论人生还是名利场,本质上都是一场又一场马拉松,就像推石的西西弗斯,看透本质却依然热爱,知世故而不世故,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英雄主义。互联网二十余年光阴,弹指一挥间,与张朝阳同时代的大佬们人人都有了自己的故事。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张朝阳的前半生故事,大概应该是这样:出生优渥,少年得志,拥有极高的学术成就,爱好广泛,经过大起大落,而后隐匿锋芒,活得愈发淡然。
不加主语单看这句话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伟大的失意者,比如苏轼、曹雪芹。前者30余年仕途生涯中,徙、贬达20余处,常常在居无定所时写下慰藉人心的诗句;后者同样多才多艺,历经家族兴衰后,留下一部鸿篇巨制。张朝阳如今的状态,与这些人的晚年亦有相似之处。这位退出聚光灯的大佬,只发动一项技能,便博得满堂彩。这像不像那个会做风筝的曹雪芹,还有那个顶级吃货苏东坡。在近年的采访中,他也表示“现在对名利看得很淡”。一个学霸大佬做老师,除了应业务需求,自然也夹带了私货。早年有诸多迹象表明,如果张朝阳没有回国“下海”,他的事业路径很可能会是一名物理学家。花有再开时,人无再少年,结果兜兜转转,绕了半生,张朝阳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区。人间有味是清欢,如今的他在聚光灯下,眼神都闪烁着光芒。这在互联网高增长神话退却,消费持续低迷的背景下,让一些卷无可卷的年轻人找到了共情点。一位知乎网友这样评价,“别的不说,2022年还有比他过得更舒服的大佬么”。小沙弥心中有佛,却未必说得佛法,没有了酒马相伴,如今张朝阳依旧不会寂寞。因为他喜欢的物理学,既是他心头的朱砂痣,也是早年那份温柔的明月光。多年以后,不知道张朝阳会不会给自己的墓志铭加上这么一段话:互联网没什么好的,也就当年追求物理知识的那份朝阳初心还行,我见朝阳多妩媚,料朝阳见应如是。(银杏科技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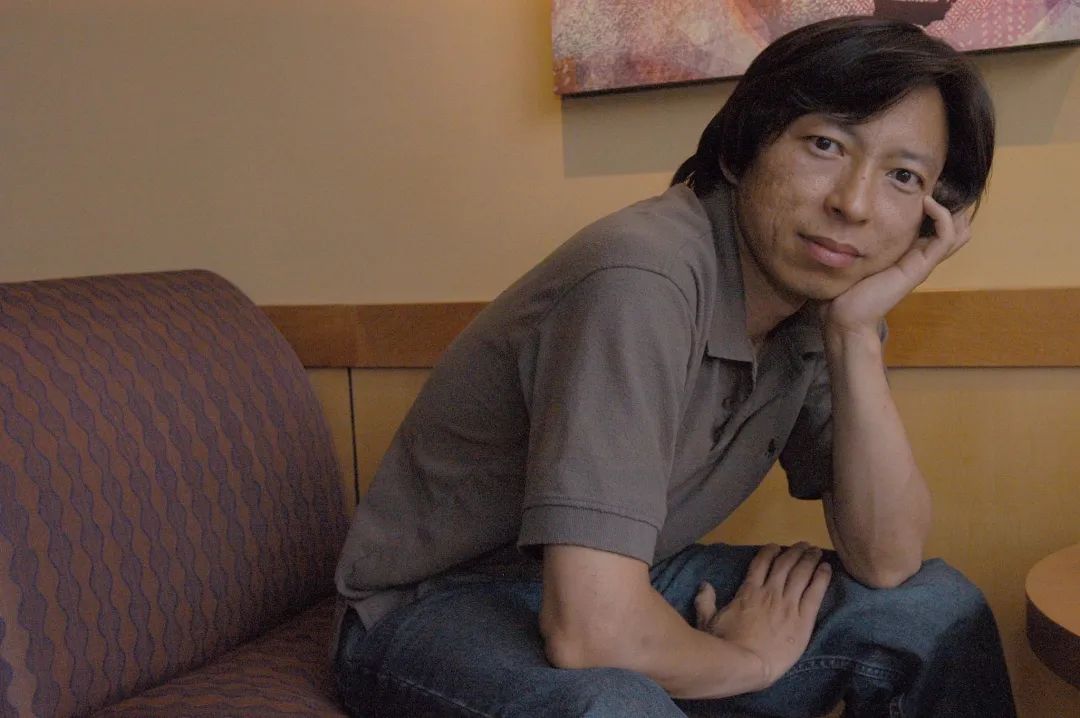



 扫码下载app 最新资讯实时掌握
扫码下载app 最新资讯实时掌握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