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距离甲辰龙年的春节越来越近,年味也一天天浓了起来。作为中国人一年中最为重要的节日,春节早已被赋予了诸多意义,而悠长假期所带来的闲暇时光,更一向是互联网厂商眼中的香饽饽。自2014年春节微信支付与央视春晚达成合作,凭借5亿元人民币的微信红包就绑定了2亿张银行卡,堪称上演了一出“奇袭”支付宝的战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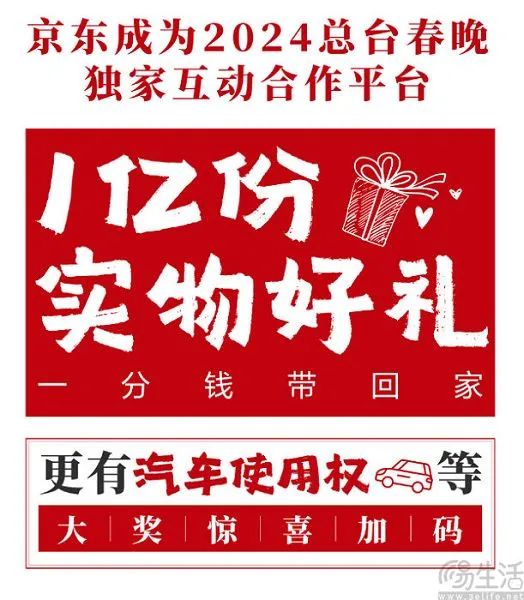
在此之后,春节期间发红包就正式成为了互联网大厂的标配,毕竟“世界上没什么事情是一个红包不能解决的,如果有,那就多发几个”。
然而在经历了2023年互联网行业将春晚赞助商的位置让给白酒品牌后,来到2024年春节,国内互联网厂商似乎对春节营销的态度发生了180°转弯。今年春节,互联网大厂似乎突然都不发红包了。
成为2024年春晚独家互动合作平台的京东,也只是宣布将以抽奖互动的形式送出一亿份一分钱奖品。但就在两年前,首次成为春晚独家互动合作伙伴的京东,从1月24日(腊月二十二)开始发放了4轮红包,并带来了价值15亿元的红包和商品。事实上,如今纵观各大互联网厂商,似乎就只有支付宝还在继续“集五福”,邀请网民在除夕瓜分5亿元红包。

如今各互联网厂商的App即使都换上了喜庆的红色,但ICON上已经鲜少见到“分XX亿”的字样。红包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,在移动支付领域,后继者微信支付凭借着“微信红包”在2014年春节上演了一出“偷袭珍珠港”,逆袭独占鳌头的支付宝,此役之后,红包成为了“网络民俗”般的存在,“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个红包不能解决的。如果有,那就多发几个。”
为什么互联网大厂突然都不发红包了,直接原因或许就是春节的潜力在过去10年间几乎被挖掘殆尽。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,在春节期间给用户发红包几乎是属于互联网大厂的专利,中小厂商则往往不会参与。难道是后者看不到春节红包的作用吗?当然不是,毕竟春节期间所产生的流量极为丰沛,但发红包也有独特的机制,因为它所关联的是支付。如果没有支付渠道,用户领到的红包就只是代金券、而非真金白银。

无论支付宝、微信、抖音、快手,还是京东,过去热衷于发红包的大厂都有强烈推动支付业务成熟、进而切入互联网金融的意愿,用户在领取红包后需要开通相应的支付业务,才能如愿将红包变为真金白银。而支付业务则显然不是每一家互联网厂商都能做的,往往只有希望打造业务闭环的大厂才有购买支付牌照的动力,而缺乏支付业务的中小厂商如果在春节期间给用户发红包,无异于是给友商在做嫁衣。
当然,现在让一众大厂不再“撒币”的根本,还是发红包本身的效费比实在太低。当下互联网行业的市场环境是冬季,降本增效、开源节流才是大家共同的选择,直接向用户发红包带来的转化和留存,已经难以满足厂商的需求。
而互联网厂商在春节发红包的本质是营销,只不过这种营销与以往在其他平台打广告来转化用户不同,是借助春节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,来将原本给广告商的钱直接送到用户面前。

以2019年的百度为例,作为春晚赞助商的百度当时拿出了10亿元发红包,手机百度也确实因此收获了上亿的新增用户。可仅仅到了初五,QuestMobile所公布的数据就表明,手机百度的留存率仅有2%。在2020年、2021年先后成为春晚合作伙伴的快手和抖音,也没能逃脱这一宿命。快手在2020年春节期间DAU升至2.8亿、随后又跌到2.5亿,抖音的DAU则在2021年春节升至5.8亿后,旋即回落到5亿。
金钱开道的玩法在增量时代显然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,而如今互联网行业早已是存量时代。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(CNNIC)在去年8月发布的第52次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显示,截至2023年6月,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0.79亿人,较2022年12月增长1109万人,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6.4%,而上一次统计的普及率则是75.6%。

就这么一点可怜的新增网民,想要在一堆厂商中截胡需要付出什么代价?高举高打、烧钱换市场的战术,在当下互联网行业中已然格格不入,各大厂商更希望的是花十块钱办成五十块的事情,而不是花五十块去办十五块的事。因此发红包就从“惠而不费”变成了“费而不惠”,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春节互联网厂商更加务实,几乎所有相关活动都是依托现有业务来展开,变得与双11期间非常类似了。
纵观今年互联网厂商的春节活动,共同的特点就是“将欲取之,必先予之”,基本送的都是旗下业务的优惠券,通过补贴优惠来吸引用户。而这样做的潜台词,就是只有成为了我的用户、才能享受到相应的福利,这显然与以往的逻辑发生了180°的大转弯。

互联网厂商已经等不及在春节吸引用户、而后徐徐图之了,现在他们更希望直接在春节就赚上一笔。(转载自:三易生活)
 扫码下载app 最新资讯实时掌握
扫码下载app 最新资讯实时掌握





